这篇文章很好,转一转
来源:2005年9月2日的《足球》报
作者:丛鹏
链接:http://soccer.goalchina.net/dianziban/ShowSoccer.aspx?id=12563
欧文,皇马一年游之后,金童回到英格兰,却有家不能回。北上纽卡斯尔的欧文双手擎着黑白条球衣,脸上挂着招牌式的微笑,可谁都知道这笑容背后有多少无奈。
克雷斯波,在AC米兰复活之后,满心以为可以留在意大利,但米兰却为了数目有限的欧元和切尔西扯皮。当米兰意外得到免费的维埃里,当切尔西得不到顶级前锋之后,克雷斯波不得不回到伤心蓝桥,还要收回对切尔西曾经的抱怨,为德罗巴打替补。
坎通纳,昔日的曼联国王,教父级的坏孩子,在今年夏天皇马、曼联相继淘金中国的间隙,孤身潜入香港,为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张代言。他得到的礼物是刘德华先生手书的三个大字:简东拿(香港称坎通纳为简东拿)。坎通纳捧着这礼物,表情茫然,没有竖起衣领,没有中指,没有飞腿。国王也要谋生,只能规矩一点。
目光回到国内足球,“奈何桥”边更是挤挤挨挨。
范志毅,被俱乐部以莫须有的罪名一再羞辱,曾经号称“范大将军”的他却没有任何实质性或气节性的反击。在下放预备队期限的最后一天,悄没声地回基地取行李,来帮忙和送行的只有一个小队员,昔日称其为大哥的一众队员早没了踪影。
张姓姑娘,谋生在南京的夜总会,陪酒、陪笑,有幸或不幸陪到一位昔日国门,一直陪到酒店房间,却因为价格问题闹到警局。事发之后,因违反“职业操守”被夜总会开除,却被别有居心的人鼓动着要打官司。当这有限的剩余价值也无从发挥之后,她就被抛到黑暗里,继续在欢场出卖青春。
《南方体育》,曾经以“有趣对抗无趣”,曾经试图以“体育改变生活”,曾经让为数不少的青年感到愉悦。后来的情形是,无趣湮没了有趣,生活改变了体育,在新学期开始之前,《南方体育》不得不结束自己的体育之旅。
足球很小,无奈很大,古往今来,概莫能外。
梵高,在绘画中找到施展他热情的天地,像农夫一样勤勉地劳作,活着的时候却只能卖出一幅画。当太阳也再不能燃起热情的时候,37岁的他把手枪顶在自己腹部,此时与他相伴的只有麦田上惊起的乌鸦,而他的慨叹是:告别是画不出来的。
科特柯本,第二张唱片就卖出一千多万张,却像梵高一样孤独,找不到他渴望的抚慰和宁静,27岁的时候开枪结果了自己。人们震惊:怎么一点先兆也没有啊?可是,如果你用心听涅槃乐队最“流行”的专辑《纽约不插电》,你就能多少感受到柯本的状态,你再听听最后一首歌“Where Did YouSleep Last Night”,怎样的撕心裂肺?
以自戕对抗无奈是更深的无奈,它令人心痛,却有一种决绝的美,但无法效仿。
还有一些人,在无奈中沉醉于自己所爱,让后世的我们在无奈中得到抚慰和力量。
杜甫,后世尊之为“诗圣”,活着的时候终生为养活妻儿犯愁,在30上下、人生最黄金的十年落魄长安,在首都只有一个暂住的身分,宽厚如杜甫者也不能不抱怨:“朝叩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”。又赶上安史之乱,举家奔逃,国家也由极盛转入衰败,无奈之深非我辈所能想象,但这一切不能改变杜甫的赤子之心。在中国的历史上,他极罕见地在40以后开始了更大的进步,晚年的杜甫是这样的萧索:“亲朋无一字,老病有孤舟”,却是这样的胸怀: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
巴赫,音乐的大海,生命的最后27年在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当乐监,当时,那个城市和那所学校并不怎么需要他的音乐,在这样的情势下,他对音乐极度的投入只会给他带来麻烦,他似乎不懂得这一点,他的幻想是:如果我把音乐做得更好,教更多的孩子学习音乐,应该会改变官方的态度。而官方的态度恰恰相反,巴赫做得越多、越好,他的处境越糟。晚年的巴赫意识到这无奈的深重,却依然执着,把生活的无奈升华为音乐的广阔和深厚。
我等凡人,在这无奈的世间多半是一种苟活的状态,简单的乐趣、朴素的关怀足以让我们活得有价值,虽然这也并不容易。
体育的价值部分是因为他在生活之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自由、更热情的天地,感动由此生发。可惜,今天的体育越来越多地被生活改变,欧文的无奈也正如这个夏天数百万新就业的青年,其中几人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?
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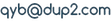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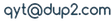
 本站的feed
本站的feed
最新评论